不再隐藏:关于无障碍策展的对话
伴随着摇滚歌声的节奏,轮椅上的人被推到泳池边,原本无法动弹的身体在落水瞬间苏醒了过来,在水中倒立、翻滚,毫无顾忌地露出纤细的双腿。岸边响起了欢呼和口哨。“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画外音中的老人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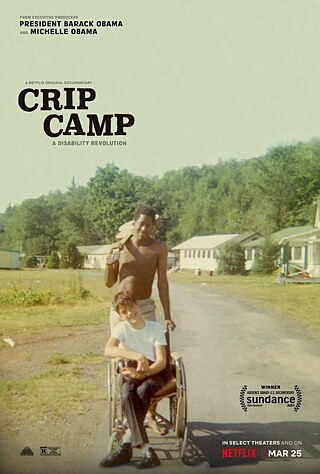
这个场景来自纪录片《残疾营地》(Crip Camp),取材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专门为残障青少年举办的夏令营。当年在夏令营中尽情享受身心自由的嬉皮士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美国残障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为残障人士的法律保护和社会参与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
影片出现在“隐藏计划”东亚区无障碍策展创意实验室的第一堂课上。当天的主讲人李耀寰(Sean Lee)是加拿大残障艺术机构Tangled Art + Disability的项目总监。受到主办方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和东亚区歌德学院的邀请,李耀寰与德国无障碍行动平台(berlinklusion)的联合创始人凯特·布莱姆博士(Dr. Kate Brehme)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带领了六场线上讲座和讨论会,与来自蒙古、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42位艺术工作者分享了无障碍策展的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共同探索了无障碍策展在东亚区实践的可能性。
首次向东亚区的同行授课,两位讲师首先关注到了残障议题的地域特殊性。虽然残障群体遍布世界各地,但不同国家对于残障的认知却大不相同。比如,李耀寰在课程中指出,北美残障者的身份认同与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权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东亚则相对较少讨论种族话题。因此,讲师们在介绍自己的策展经历之前,先用《残疾营地》等历史素材梳理了残障议题在欧美地区的发展历程,将其经验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中,而不是作为一套全球通用的标准法则来照搬。“我不想复制西方殖民时期的带有传教色彩的交流模式,告诉人们‘你要这么做’,”凯特·布莱姆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相反地,她在项目期间鼓励参与者们挖掘各自文化环境中的独特之处,并在课堂中分享自己的从业经历,在讲师和参会者之间营造双向而平等的互动。

对于项目参会者、日本独立策展人Miyuki Tanaka来说,这种互动还可以延伸到参会者的社群中,在东亚各地之间建立更加深远的连接。“能够以无障碍策展为题展开讨论已经十分难得了,能够与一群具有相似传统和价值观的人共同参与这场讨论更是宝贵的交流机会。” 在她看来,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共通性有助于在地区内部形成一股凝聚力,为基于西方的残障理念找到东亚语境中的落脚点。“向西方学习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拥有自己的声音,”她说。
然而,全线上的会议模式让这种深度交流很难在“隐藏计划”的项目期间实现。这虽然是疫情限制之下的无奈之举,但也让那些通常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国际交流机会在如今变得触手可及。蒙古国家美术馆的Mungunchimeg Bat-Erdene回忆起开课那天的心情,依然感到激动不已:“那时候,蒙古已经天黑了。我早早地就打开了家里的电脑,坐在屏幕前等待。” 会议开始后,成员们的自我介绍也让她备受鼓舞:“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为艺术的普及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像他们一样充满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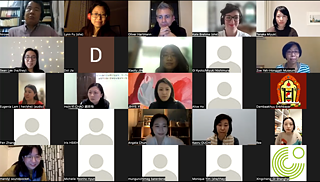
“隐藏计划”作为一个以残障为中心的项目,对残障者的服务也必不可少。讲师们在每次课程开始之前都会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衣着样貌进行简短的描述。这种描述沿袭了通常为盲人提供的口述影像,但在讲师李耀寰看来,即使我们不知道观众中是否有视障参与者,视觉描述也应该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能够“挑战人们对在场者身份的习惯性假设”——通过对盲人需求的主动关注,将残障观众纳入常规观众的范畴。
在描述自我外观时,健视者通常会用到与颜色有关的词。对此,“隐藏计划”中的一位盲人参与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Kojiro Hirose博士说道:“我其实已经不记得我的衬衫是什么颜色的了。所以,与其描述颜色,我更感兴趣的是它在我手中的触感。”这种感官的转换给课程中的另一位参与者、在香港从事无障碍艺术咨询的Liz Young Ho Man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她去拓展个体经验的边界:“当我们抛开惯性思维,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并表达我们自己?”
多感官体验也是“隐藏计划”的特邀讲师、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阿曼达·卡齐亚博士(Dr. Amanda Cachia)的关注点。根据她的观察,博物馆的无障碍服务通常是在布展结束后才开始执行的——盲文和视觉描述等补充性材料往往不是展览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很容易被忽视。为此,她提出 “创意无障碍”这一实践方法,鼓励策展人在展览的构思阶段就体现无障碍的理念;例如,观众的多感官体验既可以是作品概念中的重要元素,又能够将残障者的身体经验考虑在内,让展览在满足残障者现实需求的同时体现策展人的创造力。

然而,对于特定感官的关注,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与其对立面产生冲突。在“隐藏计划”的课程中,来自日本的Hirose博士曾建议使用全黑的空间来强化参观者对作品的触觉体验。这样的方法虽然能够唤起健视者对盲人感官的亲身理解,但也可能会给普遍依赖视觉的观众带来恐惧感。
除了策展人的想法之外,艺术家本人对作品的设计有时也会给参观者造成障碍。“隐藏计划”的另一位参与者、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兼策展人玄莲昊(Michelle Yeonho Hyun)在DAWA国际无障碍文化节期间的圆桌谈中展示了一件需要观众从洞穴式的矮门爬行进入的视频装置作品。行动不便或体型宽大的观众可以通过空间侧面的直立门进入,但这个无障碍的替代路线似乎违背了艺术家希望通过爬行来再现丛林体验的创作初衷。

“想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可能的”,韩国策展人、“隐藏计划”的参与者Choi Yeon认为。在个体差异面前,任何试图消除障碍的探索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我们能够向残障观众表达无障碍的态度,并展示我们在无障碍方面所做的努力,观众就会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馈,并为我们指出进步的方向。”这种反馈机制的背后不是一本黑白分明的行为规范手册,也不只是在某个权威给出的条条框框里打勾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基于自省和沟通的不断演化的过程,一个相互依赖的合作。
为了促进与残障者的交流,多名“隐藏计划”的参与者都在课程结束后表示他们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多地与残障者合作,无论是对参展艺术家和策展伙伴的选择,还是邀请残障者对空间进行无障碍勘察,都会尽可能地将残障者纳入到项目团队中,让残障者为自己的社群发声。
在向内反思个人工作的同时,许多参与者们也向外关注到了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刘子瑗认为,城市设施的建设是残障者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她希望能通过美术馆的融合教育活动,培养更多具有无障碍意识的学者和设计师。台湾中兴大学的Hsin-Yi Chao博士则对课程中所介绍的社会学研究角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台湾在无障碍方面的政府举措与当地文化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
“隐藏计划”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也给两位讲师带来了新的启发。凯特·布莱姆博士希望对比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残障领域的发展历史,用艺术展览的方式建立一场跨文化的对话。李耀寰作为一名华裔残障者,正在探索他的华裔身份与残障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个社群之间的交集。
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我们比以往更渴望找到连接。“隐藏计划”项目中的参与者和工作人员遍布全球四个时区,常常需要在清晨或深夜参与连线。从这个方面看,“隐藏计划”所揭开的不只是那些趋于社会边缘的残障叙事,而且还有被时空隔开的每一个个体。这些叙事与个体穿梭于东方和西方、行动和调整、平等包容和区别对待之间,为社会开辟出一片更加多元化的愿景。
作者
许梦辰是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和写作者,曾任职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残障融合教育部,并为《卷宗》《艺术论坛》《汉语世界》等中英文刊物撰稿。